任何一个主题乐园景点的设计都是从Blue Sky阶段开始。所谓的“Blue Sky/ 创意概念”阶段,就是由创意团队人员围着一张大桌子,针对主题乐园景点进行创意的头脑风暴。
它通常是这么进行的:
“等等,等等,我知道!我们可以让这些睡莲漂浮在湖面上——当然这需要在睡莲周围有一圈栏杆做扶手。人们会站在睡莲叶子上,瞄准激光,拼命将别人击倒入水。”
“那不是很危险吗?”
“不会的,工程师会想出一个办法,让激光很安全。”
“睡莲怎么漂浮在湖面上?”
“哦,工程师会想到办法的。”
——就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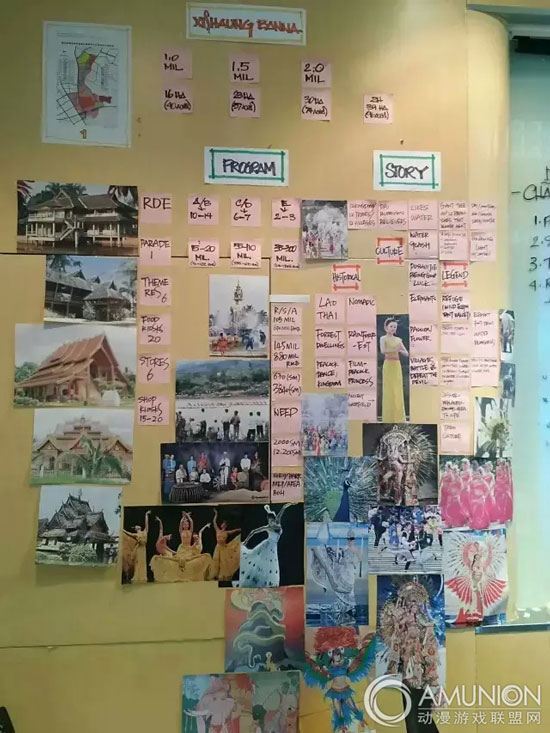
大多数景点都是从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想法开始,要么是它不能实现,要么是不可能在一个合理的成本下实现。所以,景点设计最终的结局就是变成一个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由创意团队、工程师、以及夹在其中的成本预算人员讨价还价的过程。
最终,他们会达成一个在预算内可实现的设计方案。至少,他们认为他们全无异议了。然后,工程师离开、设计一些和创意团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时候,创意团队又开始试着倒回最初大家达成一致的、那些不可能的地方。而成本预算人员会一直告诉创意团队和工程师团队不能再多花一分钱了——这是个反复进行的过程。
最后当时间、金钱、耐心或这三者都消耗殆尽的时候,景点开放了。然后,创意团队研究公众对景点的反应、对创意的反应,得出下一次改进的一堆新想法。然后,工程师们开始进入夜班模式,竭力想出办法,在不超过最初成本预算且不影响次日景点照常开放的情况下,加入这些新的东西。
因此,Blue Sky是个永不会停止的过程。Walt Disney曾经说过:只要人们心中创意存在,迪士尼乐园就永远不会终止。
那么我的“睡莲”景点到底有什么问题?——它没有故事。如果故事为王,那么在Blue Sky开始的时候就必须有故事。
例:一个城市遭遇恶魔的围困,在漂浮的睡莲上飞行的精灵族试图用“反魔枪”来保护自己,那么,我们就有故事了。我们可以之后再担心漂浮涉及的反重力如何实现的问题。
为什么这比我原来的描述更有意思?这是因为我们立刻马上感觉到这里有客观事物存在——好人、坏人两方,和一场战斗。我们会下意识的排队、把自己匹配为两方之一,大多数人选择精灵族,但我们目标市场仍有一部分人也许更倾向扮演恶魔的角色。
例:一个过山车倾斜着穿过黑暗的房间,然后越过一个微微发亮的城市上空。这景象迷人吗?算不上,因为没有故事。
例:一个去好莱坞露天剧场参加音乐会的摇滚乐团,马上要迟到了。为了赶时间,他们请你跳上他们的豪华跑车,倾斜着穿过好莱坞山,飞速驶过洛杉矶高速公路。这就是迪士尼的Rock’ n’过山车背后的故事,而这故事的确是有用的。




再看看这个例子:你爬上一个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的地下铁列车,它驶出站台,开始像地震发生一样震动。火焰喷薄而出,洪水从隧道两边滚滚而来,熄灭了火苗,在列车上方飞溅。听着令人兴奋吗?是的,但并不让人百分百满意。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在火车上,火车要开往哪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弗罗里达环球影城名字叫做“Earthquake:The Big One/大地震”的设备(是一个有解说员、乘坐电车体验电影制作幕后技术的设备),根据这个名字,当我们乘坐上去时知道该期待的是什么——但是,再没有其他潜在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参与和沉浸其中了——这个设备现在有不同的主题包装,被重新命名为“Disaster: A Major Motion Picture… Starring You”(是一个混合了黑暗乘骑、电车、表演的互动项目)。
Earthquake:The Big One



Disaster: A Major Motion Picture… Starring You




